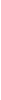脆弱
我浑浑噩噩地坐上车,甚至没有注意到,他们没有带我回那个训练基地的宿舍。当我感觉到那个熟悉的存在迅速朝我靠近时,我才意识到:
我回家了。他也回家了。
他拉开了车门,把我抱出来。
“你们对我的向导做了什么?”
他好生气。我抱紧他的脖子。这样贴近他,让我觉得多么安慰。
“是博士。”六十六说。他们放出了自己的精神体,水母的触手缠上蝙蝠。他们在交流。他越来越愤怒。好吵。
他立刻安静了。接着他很沮丧,他觉得他没有保护好我。他的手臂收紧了,他的头微微垂下,贴着我。
我又哭了出来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是爱我的,而且他没有对我做过什么恶,如果世界上不存在其他人,只存在我和他两个人,他就是无辜的。
“我累了,我们进去吧。”我说。
水母放开了白蝙蝠。它飞过我们时,翼擦过了我。
我很抱歉。六十六通过它告诉我。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道歉。我不想知道。我没有力气想。我没有力气去思考别的事。有一次,我看到海伦把一个放在冰箱顶上的瓶子取出来,倒出两片“糖”,碾碎。我问她为什么要把糖碾碎?她好像没有意识到我在那,突然听到我的声音,被吓了一下,接着她笑起来。她解释说这不是糖,这是药,治疗她自己的一种心病的药。碾碎是为了让药更好地吸收。我要记得不可以乱动乱吃哦。
她当时正在做我们的午餐。
“你想喝水吗?”他问。他焦躁,不安,希望我好起来。他沮丧。他知道怎么做就能让我好起来,但他觉得这样很……
无能。
为什么是,无能?
我躺在沙发上。“我”飞出来,飞向他。
为什么是无能?你可以。你来吧。“我”在他身边焦急地盘旋,撞向他。“我”没有表情,没有声音,没有动作。“我”只能笨拙地一遍又一遍撞向他。
直到他终于放出“他”。他向我走来,跨到我身上。他感到自己多么无能,被操纵着,被安排着,被蒙蔽着。因无能而愤怒。他抚摸我的脸,亲吻我的眼泪,我的嘴唇。“他”已经吞掉了“我”,获得了光源的水母满足地在我们头顶蔓舞它飘带似的触手,渐渐把我们笼罩。“我”也觉得很满足,因为被“他”包裹的时候,“我”最安全,什么也不能伤害到“我”。
他先进入的我,我感到我和他一起进入了我的精神空间。我从来没有这样毫无抗拒地欢迎另一个人的精神到这里来。这是一片空旷的纯白色,只有一张染血的地毯。我告诉他:帮帮我,让它消失吧。
他为我的痛苦,自己感到多么痛苦。但是他为我的这个请求,自己感到多么痛快。
“我们”飘进了这片白色里。水母优雅地缠住那张地毯,撕碎那张地毯。它会再次出现的。对精神的修整不能让人遗忘记忆,只要记忆存在,记忆可以源源不断制造许多负面感受——悲伤,愤怒,屈辱……但是,修整一下,它会暂时消失。痛苦会暂时消失。
我贪婪地抱紧他。真好。这个世界上,我拥有他,真好。
我的精神触须刺入他。
雷。我梦见过他。我不知道那是他。海伦说,那是我的幻想朋友。她也曾有过幻想朋友,随着年龄增长,幻想朋友就不在了,这是人成长的必经之路。
我失声痛哭。不该在进入另一个哨兵的精神时这样放纵自己的感情,特别是痛苦的感情。但是我不能控制。
而且他可以承受。他颤抖着,他觉得很痛,但这不算什么,不足他在“玩”那个酷刑模拟器时十分之一的痛。他的精神好庞大,广阔的图景里全是黑暗。因为海伦分开了我们。我对海伦痛哭,海伦安慰我,但不还给我,用药物控制我,摧毁我。他在冷冰冰的黑暗里等我,找我,而我渐渐地,忘了他。
现在他找到我了。把那些孤独摧毁吧。黑暗似乎稀薄了一些。他找到了我,在街头的一瞥,凭着直觉,他认出了我……可已经晚了,我已经被毁掉了。我是钝感的普通人,我也许一辈子就会当普通人,她为了隐藏我,不让他找到我,毁掉了我的天赋……所以他用刀来杀她,不希望她那么快死。
我觉得好痛苦,我不愿意——那就不要碰这些。
他引我离开那里。离开“海伦”的一切。对,不要想海伦。不要想。
想想他,想想我,想想我们。我们在一起,多好啊,我们终于又团聚了。虽然这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换来的,虽然我们今后还要被摆布,被利用;虽然实验室的实验体的身份永远烙印在我们身上——我们永远不会有孩子,有也不会给我们亲自抚养;他要执行更多更危险的任务,获得更多影响力——权力——好留住,我,利剑的锈蚀的鞘;但是,我们终于可以团聚了。
快乐。团聚的快乐。结合的快乐。性的快乐。陪伴的快乐。理解的快乐。各种各样的快乐交织在一起,把我们填满了。
爱的快乐。
所以,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真相——结束后,我躺在沙发上,这样想到。我和他最大的隔阂是海伦。把海伦的真相告诉我,不论这个真相对我来说是多么残忍,然后,在我崩溃时……把我推向他。
所以,六十六道歉。
和她没有关系,她不用道歉的。
他一边擦拭我腿间的浊液,一边问我:“你想吃什么,我去订餐。”
“不用麻烦了,营养剂。”我回答,“然后,我们再来一次。”
他有一点……有什么落空的,失落……
“我本来计划出去吃,”他解释说,“电视塔的旋转餐厅,我查到那里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夜景。”
我不想故意扫兴,但是……要是他们没做这样的事,让他能按计划带我出去吃晚餐,我一定没心情欣赏夜景,只会觉得那场面很尴尬。
接着我听到他说:“今天是我们的生日。”
“我们……的生日?”
“也许,不该说是生日,是我们剪去脐带的日子。”
我沉默了一小会。
“我们是怎么出生的?”我问。我没有抱太多希望,我得到的回绝太多了,已经习惯。
他果然犹豫了一下,这是不该对我多说的话题。
可他多说了:“我们是互相比对着编辑出基因的受精卵,完美契合的两个个体,为了培养默契——他们这样形容——我们被放进并排放置的培养皿里一起分裂分化成型,然后放进同一个培养水箱,一共十叁个月,之后被捞出,剪断脐带,用自己的肺呼吸到第一口空气的。有一张照片,他们,实验室的全体成员,二十叁个人,和我们。”他笑了一声,“他们算是我们的父母,二十叁个父母。”
现在,我知道了另一个答案。
我的父母在哪?我问海伦。她哭了。
我想,如果我没有被雷找到,我继续和她过普通人的生活,她是否真的会在一个合适的时候,告诉我一切的真相——我没有父母,她为了她的某种目的,把我从唯一可算是我亲人的我的哨兵身边带走了。
她让他那么痛苦。她让我……
我捂住眼睛。
如果我一直是普通人,我不会感到任何落差。我不会感到自己被毁掉了什么天赋。我感到的只有:她的爱。
她真的,我真的……我把她看做是我的母亲。